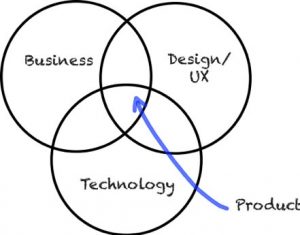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其实很少有针对产品管理的课程,可能最接近的就是MBA了。我接触到的很多谷歌产品经理也都是“半路出家”;对于如何给产品定价,大家几乎都是通过实践而逐渐积累得来的。
我刚刚转型产品经理的时候,其实一度“小看”了定价的学问。当时的我以为定价只是简单的成本和利润的计算。我一直觉得只要做好产品,就一定会有人买单,具体的价格只不过是一些细节。直到我真正参与到很多产品的定价,从0到1的产品案例,以及给PaLM 2和Gemini模型定价的实践中,我才逐渐体会到定价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你的产品定位、价值主张、市场策略、品牌形象的综合体现。
尤其当你面对一个从0到1的创新产品时,这个问题更是难上加难。市场上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可供参考,没有现成的商业模式可以借鉴;你的产品就像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如何为它标上第一个价值标签,并且让人们为之买单,背后其实充满了学问。
一般来说产品定价有3种不同的思路,基于成本的cost-plus,基于价值的value-based,以及针对市场和竞争的competitive-based。Cost-plus顾名思义,就是在成本之上再多加一定比例的利润,适用于大规模生产、技术壁垒不高的产品,比如我们的日用品。Value-based则注重产品为用户解决了什么问题,创造了多少价值;比如Document AI就定价处理一张ID的价格在1美金左右,因为在没有AI和自动化以前,人工手动处理、鉴定并核实一个ID需要2-3美金,这就体现了节省下的30%-50%成本。而最后的Competitive-based就侧重于让产品更有价格上的竞争力,能够有效地获取新用户,但同时也很容易引发价格战。
在做大模型的初期,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定价低于 OpenAI 一半,吸引更多用户尝试。但副作用也很明显:由于模型在个人用户体验上的质量不够好,市场很快形成了“谷歌模型便宜 = 质量不行”的印象。但事实上,因为谷歌从训练模型初期就不会收集用户数据,所以对于个人用户使用场景的积累有些慢。但对于企业用户这边就好很多,因为有非常多信任的大客户和伙伴,我们拿到了很多企业场景的范本和数据,都用在了模型的后期训练中,所以最开始的PaLM 2模型和Gemini 1.0 / 1.5在企业用户中得到了一些不错的反馈。
2024 年,整个大模型市场陷入激烈的价格战,各家都在不停降价。我还记得很清楚,每隔2个月,我的一个惬意的清早就会被OpenAI的降价新闻扰得鸡犬不宁,之后一周的工作就是反复计算新价格,分析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并且要用最快的速度拿出对应的方案。直到 Anthropic 3.5 出现,它的价格不降反升,这才让这场“race to the bottom”的闹剧画上了句号。随之,Gemini在2.0和2.5的时候都提高了价格,OpenAI也是如此。
因为谷歌的模型价格一直都是最便宜的,所以当我们在提价的时候,就造成了不小的颠簸,尤其是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很多大客户刚刚签订了购买比如100万Token的订单,结果因为涨价现在就只能用50万甚至更少了。销售和法务团队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管理这些企业用户上。当然,这样的价格战就像之前国内共享单车、打车app类似,对于广大个人用户来说是收益最大的,直到市场重新恢复理智。
相比之下,我更很喜欢的定价策略像是特斯拉一样,先从高端的型号开始(model S, model X),这样可以尽最大的能力提高利润率,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保证公司现金流的稳定,然后再投入到量产的中端型号汽车。同理,苹果的iPhone手机,XDR显示器也是如此。这次,谷歌的路径恰好相反,这其中原因有很多,但因为公司的家底丰厚,才有能力承担这样的风险。如今,随着模型质量的不断提升,谷歌对Gemini的定价权越来越多,一切都走回了正轨。
如有说让我回到过去,可以重新给Gemini定价,我可能不会把价格设定到比OpenAI低50%,而是持平或者略微便宜。不过很多时候,市场的洪流会把你推向某种选择,就算是一样的价格,价格战可能还是会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不理性的市场中找到锚点和一个可以延展的定价架构。
写下这篇博客有几个小小的原因,一来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并且想分享Gemini 模型的定价的经验和亲历价格战的感悟。产品定价,既是战略选择,也是市场博弈,更是产品经理必须修炼的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