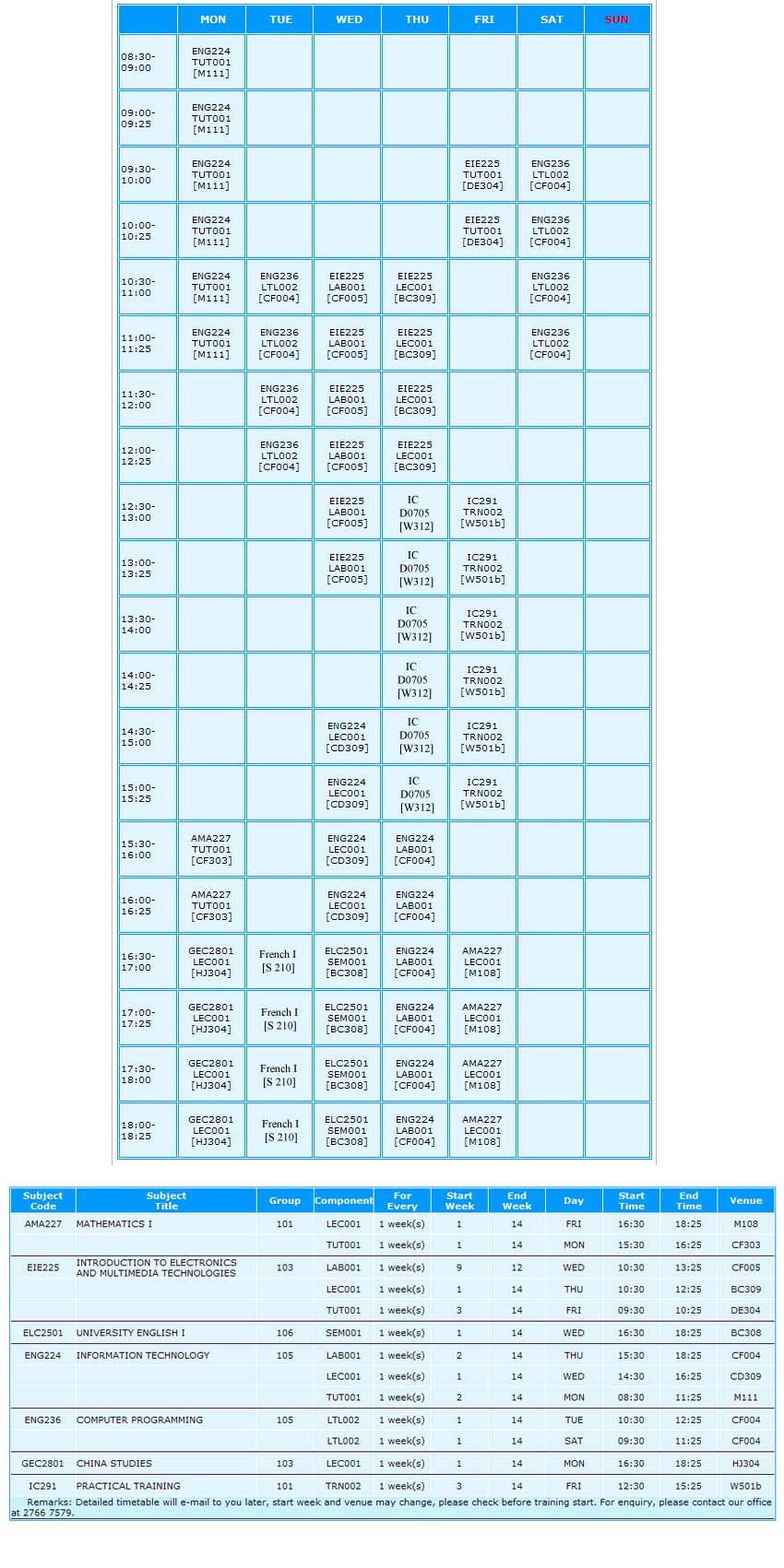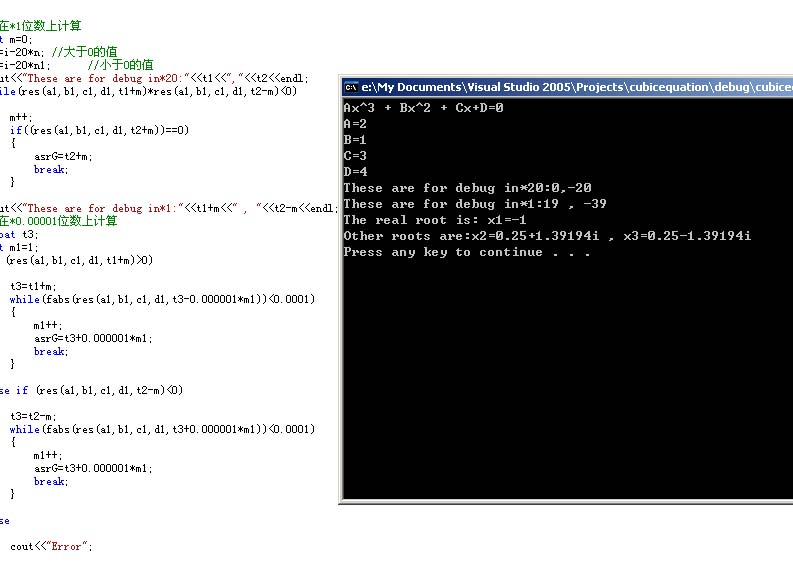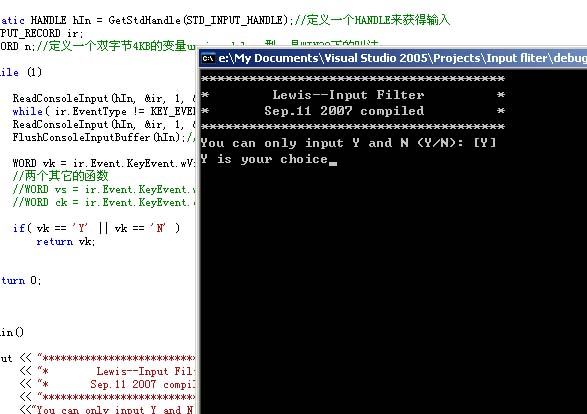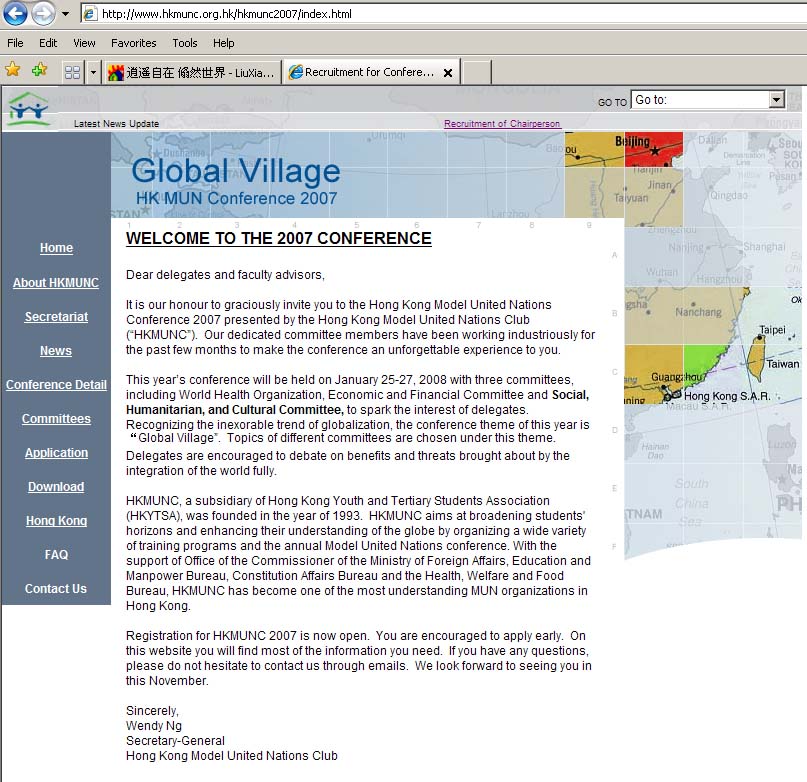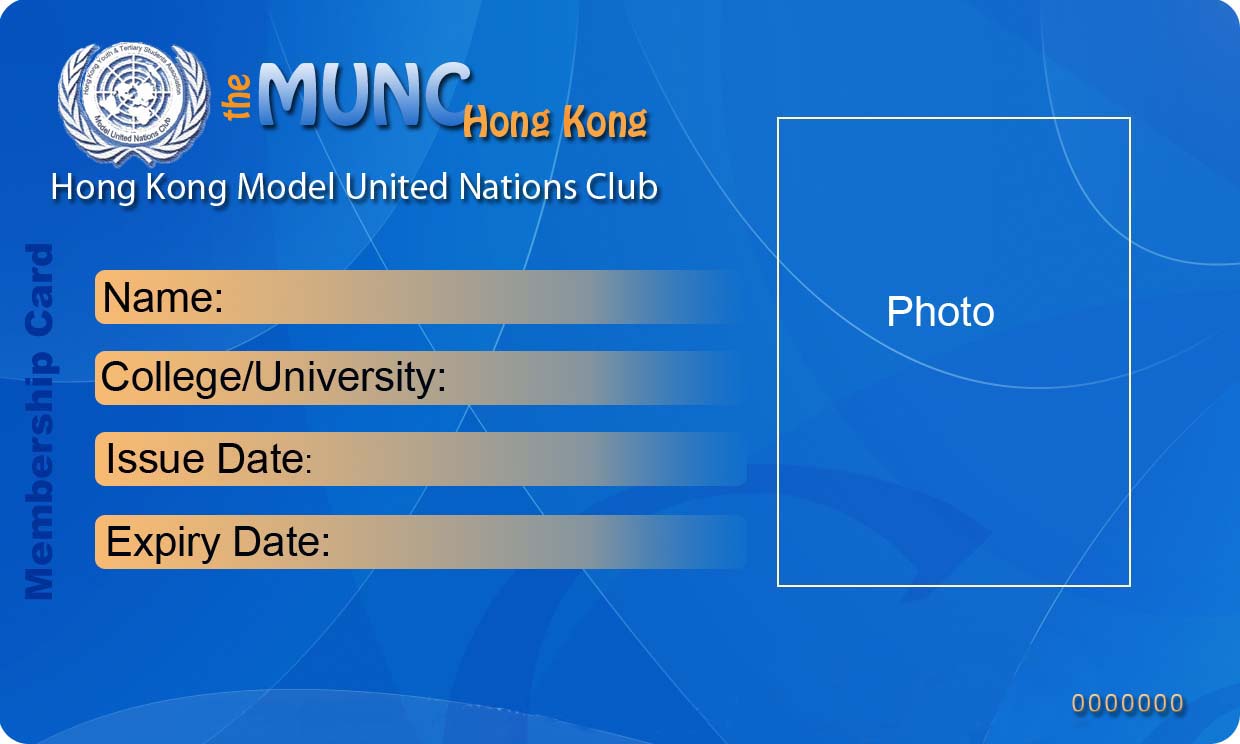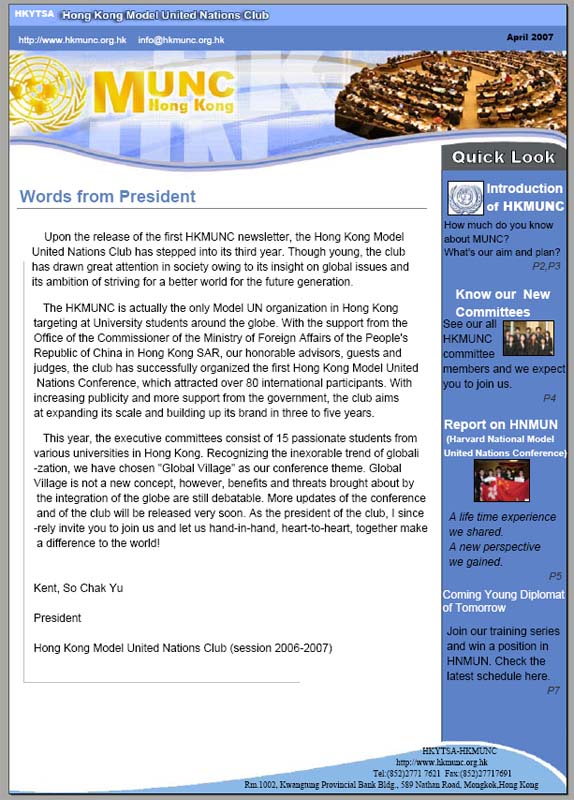把九寨沟放在第一个介绍给大家是因为它是“比较下”让我最满意的旅游景点。不过在正式介绍九寨沟之前,还是想在到外地旅游的层面上给大家几条建议:
1.到目的地报团
我们就是在到达成都后,在成都的中青旅参加旅行团的,这样有两点好处:一个是要比我们从北京报团节约不少银子;二是能够更好的安排行程,因为很多旅行团团费包含了机票,这样往返的机票是定好了,行程必然十分紧张,很少有自己能够支配时间。如果到当地报团,才能真正享受。
这样又带来了两个问题:
机票
在网上订就好了,预定时间约早所能享受的折扣约多,而且价格并不比旅行社的贵多少。但是还是要货比三家,因为有些价格在国航网站买不到,却可以在携程买到;而有些票在E龙比携程便宜。
酒店
酒店也是我们在网上直接预定是如家连锁酒店,因为这样的连锁在品质上有保障,而且价格也比较公道,所以很受到背包客的青睐。同样还有很多,例如Motel(莫泰)等等,当然我们到了成都后发现当地还有价格更便宜的当地连锁酒店,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不要预定过长时间,如果有更好的酒店可以换,如果没有到期后再延期即可。
2.距离近的景点可以包车游览
我个人不是很愿意参加旅行团,原因太多了,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不一一说了。我们通过成都的中青旅包了一辆面包车,一天是200元。这样我们10点30出发,一天游览了青城山和都江堰,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从青城山步行下山的时间。如果参加旅行团是肯定缆车上下的,要不就是一大早出发,把行程塞的满满的。
包车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确定好所坐的是什么车,是面包还是桑塔纳什么的,另外还要协商好高速公路过路费、过桥费等问题。
当然像九寨沟这样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参团去,因为路是在是比较难开,时间也很长。
3.尽量避开旅游的热门线路和旺季
这次去四川旅游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真的感觉是去看人了,而不是去享受去了。无论在九寨还是乐山,人真的多得不能再多。旅游好像不再让我感到很惬意,更多的是烦躁。九寨沟我就不建议大家在旺季去玩,如果可以选择淡季去更好,因为那里人多的让你感觉不到“人间天堂”。
下面进入正题介绍一下九寨沟:
目前有两种团,一种是双飞3日团,另一种是汽车4日纯玩团。我建议大家参加第二种,虽然会在路上花费很多时间,但第二种团有二次入沟,其次没有安排购物。在九寨购买的门票是220元,包含2次入沟的费用,如果你选择飞机3日团,就只能浪费2次入沟,关键是一天你不可能把九寨沟转完,只能做汽车草草逛一遍,在景点照照像,根本不能徒步走走栈道,享受周围的环境。
很多人去了九寨沟都感觉如同天堂,但我和家人却没有那么明显的反映。九寨沟入沟后很多树林都是次生林,也就是说在砍伐后种的,虽然覆盖率很高,但与我在德国看到的森林是天壤之别,在德国我们看到的森林是很粗大的大树,进入林子后感觉阴森森的,很幽静,但在九寨沟却不是这样的。当然人们都是说来九寨是看水的,的确九寨的水很漂亮,有很多瀑布,浅滩,湖泊(海),由于水中富含矿物质,水碧蓝碧蓝的。后面我会附上照片让大家一睹为快。
再有我想介绍一下九寨的两日的玩法,九寨沟成一个”Y”字型,入口在下面,所有景点都集中在右面的岔路上。很多导游会建议大家利用第一天主要乘车把所有景点过一遍,然后利用二次入沟的机会再游览一下。不过我不建议大家这么玩,因为如果不是天气照不了好照片的原因,这些自然景观看过玩过一遍就可以了,倒不如利用时间好好享受一下步行在树林、小溪间了乐趣。所以我们第一天仅游览的右上面的一条沟,多数以步行为主。而第二天一早我们乘车直接到左上方的沟向外游览,因为左面那条沟只有两个景点,所以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景点都是风景也没什么值得介绍的,所以大家还是后面看照片吧。再说两句所需要带的东西:
雨伞(沟里十里不同天,很突然下起大雨)
长袖外套(我们是8月去的,沟里温度是18度左右)
以上就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与提示吧,下面是九寨沟的介绍:
九寨沟位于岷江上游阿坝州南坪县境内,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50公里,因沟内有盘信、彭布、故洼、盘亚则查洼、黑角寨、树正、菏叶、扎如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
九寨沟总面积约620平方公里。其中52%为林木繁茂的原始森林。自然景色兼有湖泊、瀑布、雪山、森林之美,有“童话世界”的美誉。大多数景点集中于“Y”字形的三条主沟内,纵横50公里。根据专家的考察,这种高山湖泊是在地球新构造运动中,地壳发生急剧变化,山体不平衡隆起和河流侵蚀作用形成的。分冰川剥蚀、岩溶洼地阻塞湖、泥石流堰塞湖、滑坡与崩塌堰塞湖四大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水色清澈透明,幽静深邃,彼此以台瀑相连,逶迤不绝,小的有半亩,大的有千亩以上。四岸有千年古木,奇花异草,四时变化,色彩纷呈,倒影斑斓,气象万千。其中最大的长海,长7公里,海拔3000米,澄如碧潭,冬可滑冰,夏可行船。临近的五花海,由于湖底有各种色素的矿物质和枯枝败叶、海藻等沉积物,经过阳光的折射,幻出丰富多姿的色彩,成为名副其实的彩色湖。
九寨沟现已规划为:树正景区(火花海、卧龙海、犀牛海、古磨房和树正瀑布);日则景区(珍珠滩、诺日朗瀑布、珍珠滩瀑布、高瀑布);剑岩景区(天鹅海、悬泉、剑岩原始森林、熊猫海);长海景区(长海、五花海、上季节海、下季节海);扎如景区(骑马、野餐、藏族村寨民俗)等几个景区。已开发出二滩、三沟、四瀑、十八群海。最著名的景点有剑悬泉、芳草海、天鹅湖、剑竹海、熊猫海、高瀑布、五花海、珍珠滩瀑布、镜海、诺日朗瀑布、犀牛海、树正瀑布、树正群海、卧龙海、火花海、芦苇海、留景滩、长海、五彩池、上、下季节海等。各景点之间栈道幽深,小桥横跨,村寨古朴,民风各异,令人有飘然出世的超凡脱俗之感。妩媚的春日,九寨沟众多景点万紫千红;炎炎夏日,则浓荫滴翠;醉人之金秋,则五彩斑斓;严寒隆冬,其景色则冰清玉洁。真可谓四季分明,各有千秋,其中尤以金秋最为迷人。
深藏在林中的108个高原湖泊—海子,每到其时,天高气爽,碧水澄澈。映衬着漫山遍野绚丽多彩的秋林,水底五彩石,天上飘白云,如梦似幻,如醉如痴。火花海、五彩池等景点因池水清澈,湖底石质晶莹而折射阳光,呈现出梦幻似的光彩,步移景换,犹如进入了童话世界,珍珠滩水波粼粼,如飞珠碎玉。诺日朗瀑布宽达100余米,从30米高的石崖上,飞泻而下,色彩明艳,另具一番秀雅自然,清纯优美的风韵。
九寨沟的森林2万余公顷,在2000米至4000米的高山上垂直密布。主要品种有红松、云杉、冷杉、赤桦、领春木、连香树等。在这里的原始森林中,栖息着珍贵的大熊猫、白唇鹿、苏门羚、扭角羚、毛冠鹿、金猫等动物。海子中野鸭成群,天鹅、鸳鸯也常来嬉戏,是我国著名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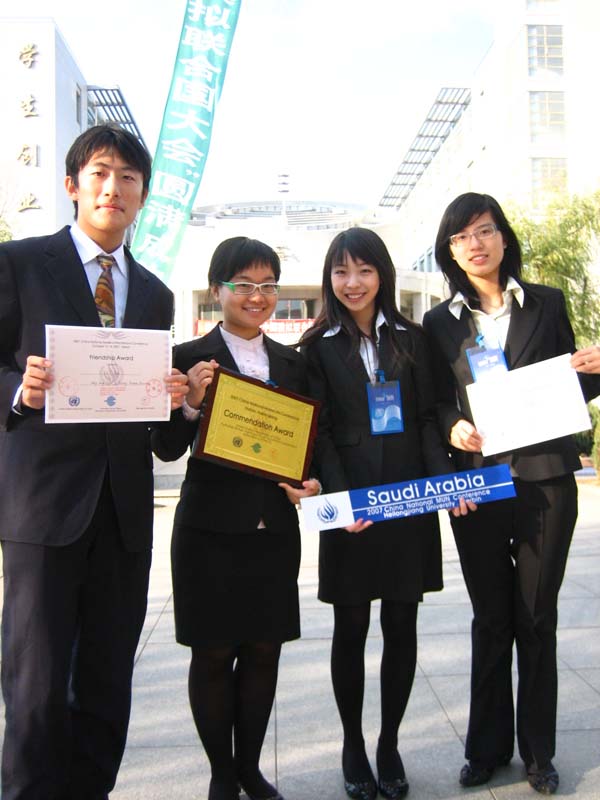




 !第一局是一个实力很强的直板选手,不过我还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14:12,11:2的比分获得胜利。然后就是不是我球技问题了,而是RP的问题,我下一组的两个参赛选手都没参加比赛,结果我就直接晋级8分之一比赛了,对手是校队的,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2局赢3球,结果赢了六个球,哈哈(标准很低啊~
!第一局是一个实力很强的直板选手,不过我还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14:12,11:2的比分获得胜利。然后就是不是我球技问题了,而是RP的问题,我下一组的两个参赛选手都没参加比赛,结果我就直接晋级8分之一比赛了,对手是校队的,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2局赢3球,结果赢了六个球,哈哈(标准很低啊~ )不过怎么说也是8强,嘿嘿!
)不过怎么说也是8强,嘿嘿!